赵汉奇,生于归绥,殒于归绥。身为民族脊梁,国战英雄,因为种种原因,大陆鲜有提及(笔者也是去台湾接触到国军后代,偶然聊起绥远往事,方知昔日归绥曾经出过如此英雄人物)。在台湾,有说他和平投共晚节有亏,有说他戍边新疆抵御外侮,实属民族功臣。
面对深陷历史迷雾中的民族英雄,加之其坟墓就在呼和浩特东郊,笔者好奇之余,查阅两岸关于赵汉奇的史料,以及赵汉奇儿子的回忆文章,实地走访赵汉奇出生村落的亲邻故旧,希望用接下来的一系列文章,还原出赵汉奇在那一个时代中的人生轨迹,以及他身后两任妻子及后代的浮沉命运。
引子:百战余生多磨难 枪底游魂心不甘

滕家营子,是归绥东郊的一个村子。
1949年后,滕家营子改名为腾家营村。
从满清到民国,顺官道到归绥京城,或者经白塔车站沿平绥铁路去包头大同,都要经过滕家营。
连接滕家营子和归绥城的官道,是一条土路。
民国年间,归绥近郊土地均为私人及召庙所有,土路弯弯曲曲,穿过田野,绕过水塘,城东十里八乡的,都要在这条路上经过,自然,北洋军,日本人,八路军,晋绥兵,解放军,也少不了在这条路,这个村子留下过兵的印记。
午夜,邻近滕家营子的官道上,从归绥城往来的方向,一辆驴车咯吱咯吱的向村子的方向移动。
1952年,新政权已经成立两年有余,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往日夜间出没路旁“请财神”的土匪早已亡的亡,逃的逃。社会治安好了很多,但是信奉“夜不出户,守望相助”乡村古风的庄稼汉,基本都是随着太阳作息,除了有事,很少半夜出门,因此,寂寥的夜里,驴车声伴随着驴脖子上的铃铛声,分外清晰。
那一颠一颠的驴车前面,是一个赶车的中年男子。借着月光,隐隐绰绰能看见驴车上的草席包裹着一个人。
赶车人姓杨,家族世代居于滕家营子,他和在后面跟车的中年人是兄弟俩,也是躺在驴车上的赵汉奇的舅舅。
春末夏初的光景,村里的庄稼汉们都早早下地抢忙农活,尤其是前一两年分了土地,现在都是为自己的田地忙碌,恨不能一天当成两天忙。但是对于杨氏兄弟俩而言,他们不仅不能忙农活,还得在农会干部鄙视的眼神中,接下进城收尸的任务。
哥俩走了长长的一截子路,离滕家营子很近了,哥哥这时候驻足脚步,左右打量了一圈,路旁残破的土围子,是前两年解放军攻打国军刘万春部时留下的痕迹,墙围子上生石灰书写着斗大标语“打倒美国狼,保卫新中国”。
午夜的月亮,悬在头顶,惨白清冷。前面的路分了岔,沿着岔路不远,有间小房子,相伴着路旁的墓园坟地。村里的人下葬死者的时候,为避免雨打风吹,就造了这简陋的小屋,方便暂厝亡人灵柩。
“快到了”哥哥用鞭子指了下路旁小屋。
驴车上,魁梧身材的赵汉奇,一卷草席盖不过来,双脚耷拉在车尾。
兄弟二人,推开木扉,将包裹着赵汉奇的草席抬到屋子里,轻轻平放在地上,点上一根蜡烛,微弱的烛光下,两个舅舅陪伴前往黄泉路上赵汉奇最后一程。
弟弟找出锨镐,欲去屋外挖坟坑。而年长的哥哥,心有不忍的蹲下身去,轻轻掀开蒙在外甥赵汉奇身上的草帘。
哥哥把一只手搭在赵汉奇头上,用劲地缓缓抚摸着,他低声说,”人人都说你在外面,为国立了大功,做了大官。钱有了,小老婆也讨上了,眼瞅着甚都好好的,怎么就……”言语哽咽处,两行泪潸然而落。
舅舅的泪水滴在赵汉奇的脸上,包裹在草席中的赵汉奇,身体轻颤,苍白的嘴唇微微张开,艰难地翕动着,哥哥急忙叫回弟弟,弟弟扔下工具,趴下身去伏在赵汉奇身上,是听心跳,还是在听汉奇临终的话语?
枪决赵汉奇的时候用的不是炸子,子弹从头部穿过时,从右边小脑打进去,从右眼角打出来,伤口很小,流血也不多,当时趴在身上还能听见心跳,俯到鼻边还能感知到微弱的呼吸。只是赵汉奇的喉咙里像被布团堵住了一般,不甘地呃呃不停。
当年的国之栋梁,国家元首亲自颁发勋章的民族英雄,为更迭的朝代所收割,奄奄一息,躺在草席上,等待天国的召唤。对于经历黄埔熏陶的革命军人而言,既然已经置生死于度外,那么生活本身的荣辱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曾经的国战,阿克苏城头的枪林弹雨,付出了众多袍泽的生命代价,保家卫国在所不惜。
时空凌乱,经历坎坷;初心犹然,肉身凋零。对于此刻的赵汉奇,该记得怎么就忘记了,不该想起的怎么偏偏浮现脑海,经历与冒险,荣誉与污名,选择与坎坷,父母,两任妻子,十个子女……一生如电影般瞬间闪回,转瞬间,大脑细胞渐次枯萎,回忆的潮水旋即褪去,那每一个枯萎的细胞,每一处凋谢的回忆,可曾突然勾起了赵汉奇心里的创痛?
蜡烛燃尽,只剩下一小滩白色的烛泪,一瓣叠着一瓣,像一朵白色腊梅。腊梅的花心中间,一缕青烟,升得很高,在空中荡漾着。
历经了倥偬戎马,百战余生的赵汉奇,走完了他不到四十年的人生路,从顽皮少年到民族英雄再到反革命份子的一生,一个军事奇才,殒命于政权交替之后,横死(非正常死亡的意思)的他,只能化作一抔潮湿黄土,静静地守望着他出生的故乡。
两个舅舅,默默地赶着驴车,缓缓前行,迎着晨曦,回到了滕家营子。
土路穿过滕家营子,一直通向东方天际的地平线,那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备注:这是一个军事奇才的谢幕,也是追述他一生传奇故事的开始,主角是一位英雄,笔者并不是去讲述英雄主义的轰轰烈烈,站在赵汉奇的墓碑前,听着赵汉奇的表弟讲述赵汉奇生平,昔日的起伏飘零,与今日的追述回忆,这之间是一种微妙的拉锯,用龙应台的话说就是记忆特别容易消失,要把它找回来,则非常费劲。

图为赵汉奇表弟杨大爷给大胡子青蛙讲述他父亲及自己看护赵汉奇青冢,因村庄修路改造等原因三次迁坟,并在坟茔后种上杨树方便赵汉奇后人访祖祭奠。

看着赵汉奇墓后郁郁葱葱的杨树,坟茔上的青草,绿了又黄,而赵汉奇的生平,却越来越少有人述及,但是如果连这样的回忆也没有文字记录的话,那这一段坎坷凋零的历史,就更难留下任何被书写被记录的痕迹。
四十年来家与国,折戟沉沙化作尘。壮士空余西域心,一抔黄土映斜云。
2016.06.18 写于呼和浩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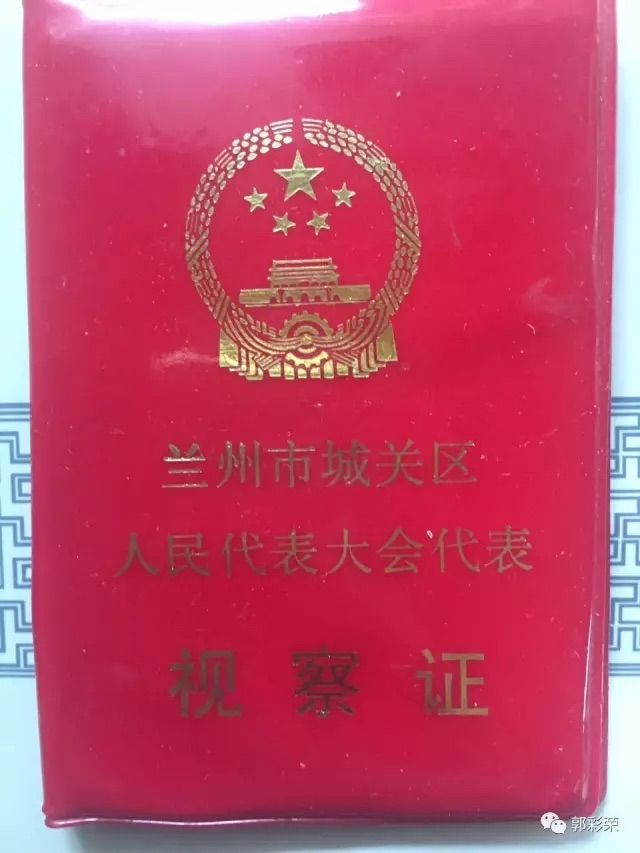


One Comment